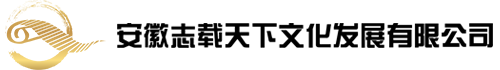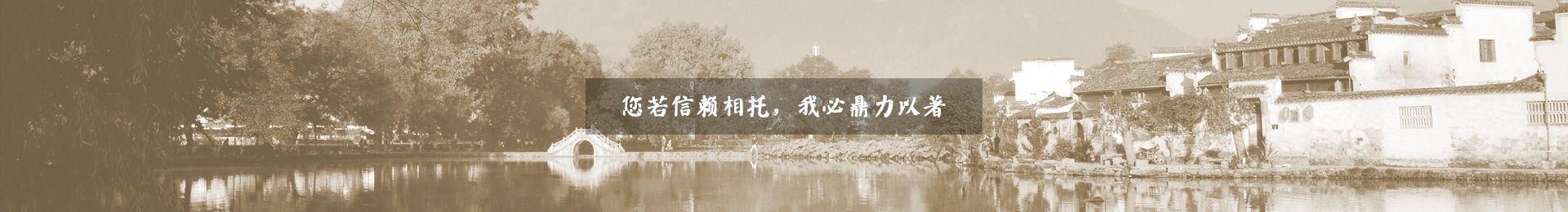【摘要】 中国地方志书的表述乃以中华母语为基础。举凡旧志皆以文言,社会主义新方志所使用的语言主要为现代白话。说“主要”,意即其语言使用非唯白话,察当代万余部面世的新方志,多有文言糅渗其里,与白话并用。虽然全国一、二轮修志弃用“文白混杂”,这种观点亦为广大修志者所秉持恪守,但当代志书里大量“文白”并用乃客观事实。
之所以究其“文白混杂”,盖我们对母语的渊源及其历史发展未去作理性研究,以及对新方志的语言现象未进行查察所致。本文由“文白”之异同、新方志的文言现象以及文言与当今白话的走向阐析,旨在陈说母语之于“白话”的传承性。
【关键词】 志书语言;传承母语;文白关联;论说
一、文言及其“文白”异同考
地方志书的性质所决定离不开大量历史史料,自然也离不开汉语的语词表述,但在当代方志行文中能否使用文言上思维一直呈“窄化”状。对于“文白”,其属性界定的清晰与否决定着新方志语言的自如运用。
(一)文言的前世今生
辞海释义:中华母语指本国语言。亦即汉语、汉族的语言,又称华言、华语、唐话,是中国通用的官方语言,属汉藏语系。最早的汉语文字约在公元前14世纪的殷商后期出现,此时形成了初步的定型文字即甲骨文。若从甲骨文算起中国有文字史至少3600年,从人文之初便被创造出来并加以使用。自秦一统文字后虽然中国各地口语表达不尽相同,但在交流中有了各民族统一认知的法定文字,以致中华后来才成为承前启后而能够治理、统一的一个整体国家。
商周以降,广义汉语的外延一直包括口语和书面语两个部分。在当代,古书面语被称之曰文言文,今书面语被称为白话文,以现代汉语为规范。
文言文乃民国及古代时期书面语言的唯一形式,承担了中华几千年的文化记录与传承的任务。文言地位的式微肇始20世纪初以陈独秀为代表的“白话文运动”,成为了近、现代古汉语颓衰的“陪标”品。
文言在中国通用了几千年,没听闻不能准确表达天下、国家、社会、家庭、私人的联系、沟通的道理和事物。究其实文言几千年的稳定性对中国语言的发展起有一定乾坤的作用,使汉语在以后行进过程中不至走离太偏,从而保证了后人赓续承传中国的优秀文化。这一点之于当代更为重要。
和中国文明同时期的世界其他几大文明的消亡皆与此有关。语言的不稳定、变化太快,使得文化成果不能得以有效传承,历时久之,这些国家的文化就自然的衰微进而走向消亡。中国正因了文言,中华文化得以传承5000年,历经多少风雨沧桑迄今依然屹立世界民族之林,而同时期全球的另三大文明古国只撇下一堆遗址。中华几千年之所以不分裂,一统的汉语功不可没。其中,能凝聚全球华人包括“港、澳、台”有着不同方言的人具有着相同文化认同的主因,当归功文言。
在全球,当下中华母语被世界占1/4的人口使用着,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国际地位不断上升,汉语受到热捧,许多国家均成立有孔子学院,其中中文是非常热门的一项专业,而中国的古文、古诗词等传世经典也深受老外的青睐。中国文化的刚柔并济、博大精深,深得全世界人民的认可,愈来愈多的人学习中文、研究中文继而探索中国的国学和传统文化,这也更佐证文言其实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标识之一。
稳定的文言解决了不同地域、不同时空人们的交流问题,对中华母语的启蒙、发展、佐辅、匡正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中华母语发展至今,看似文言已经走向了“末路”,而事实上它已融入了现代白话之中,正是“不废江河万古流”。如果今天不对当代语言上的谬误认知予以辨识,100年后再回头来看,“五四”运动前后定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断层。
但是,在新方志语言的运用上至今我们还在迷惘,今天我们修志的观点深受使用文言是否为历史倒退的滞碍。纵观几千年大浪淘沙的历史,其中能保留下的文言终究是国粹、是精华,精华的东西我们就应该批判的接受并加以弘扬。以历史传承的角度察之,并非古老的东西都是落后、落伍的,就已经应用了3000多年的文言而言,它正是中华母语屹立几千年的中坚和最具支撑力的“脊梁”。
(二)文言与白话之异同
文言与白话的界定,徐时仪在《汉语白话史》中论:“‘文’谓‘文饰’,‘文言’本为‘华美之言’义” ①。王力则对“文言”进行了具体的论说:“‘文言’用于指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言以及后来历代作家仿古作品中的语言” ②。
“白话”名称的出现较晚,“白话”中的“白”乃由戏剧中“说白”的“白”发展而来,后用于指唐宋以后以北方话为基础而形成的书面语言。白话包括古白话和现代白话。吕叔湘根据文言和白话两种不同文体,以晚唐五代为界,将汉语界分之前为古代汉语(文言)和之后为近代汉语(白话)两个阶段。后又有学者将汉语史分为3个阶段,具体时间界限为:晚唐五代以前的古代汉语(文言);晚唐五代至“五四”(也有学者认为下限为清初)的近代汉语(古白话);“五四”至今的现代汉语(现代白话)。
① 徐时仪,《汉语白话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② 王力,《古代汉语》,中华书局,1999年5月版
由是析之,文言与白话二者间既有区别又相关联,是同为中华母语在演变发展过程中的两种不同表现形态,彼此也存在着相互吸纳和渗透。徐时仪认为无论是文言占统治地位时还是白话取代文言后,二者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无法截然分开①。这种说法非常恰当和形象:一方面表明了文言与白话的关系微妙,无法一刀切开;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文言与白话能够和谐发展、互为依附。从而得出,文言与白话这两种表现形式只要运用得当,就具互补性。
为弄清古今书面语和口语的问题,我们需先界定古白话的概念。
在汉语史上,上古汉语和近代汉语之间尚间隔着一个阶段“中古汉语”,指的是从东汉、魏晋南北朝到隋朝、唐中晚期。在中古汉语阶段书面语和口语已经有了距离,书面语是模仿先秦和西汉的文章,而口语却一直在发展。既然中古汉语阶段书面语被称为“文言”,那么,那个阶段以后的口语在当时也就被人称之为“白话”。这种“古白话”由于比较接近当时的口语,其语言与当时仿古的书面语不同,因之就统称其为“白话”。
从汉语史的研究角度,中古汉语确实是一个独立的阶段,它上承上古汉语下接近代汉语,和二者都有联系,但又都有区别。
至于文言和白话之关系,一方面,语言发展既有阶段性亦有其继承性,上古汉语的词汇语法有不少至今还保留在现代汉语中。另一方面,大量历史文献告诉我们,典型的文言作品和典型的白话作品都有,但文白夹杂者也居一定数量。譬如唐代张鷟的《朝野佥载》就是文白夹杂,叙述是文,对话为白。同时文言和白话的书面语和口语也并非壁垒森严、截然而分,而是会互相影响和渗透。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肇始,应当说文言与白话既是一对冤家对头又互为浸渗。因为两者曾为了书面表达权而相互“争斗”不休,但论争的结论是,几千年来文言“在朝”、白话“在野”,二者并行不悖。而且在大量古代文乃至当代文中,我们经常可以发现白话与文言的“亲密接触”,甚至是磨合的趋势。
二、当代志书的文言现象
新编方志一方面力避“文白混杂”,而另一方面又追求语言凝练、“文约而事丰”“夫叙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日省句,二日省字”(刘知几《史通·叙事》),即要求文字简约却又强调内容丰富。是乃矛盾中之求同。
尽管新方志行文摒弃“文白混杂”,但当代志书语句中在大量使用文言却是不争事实。譬如由古而延及至今的字词:毗、邻、阴、阳、五、岳、犬、康、庄、鸿,雁、还、回、
① 徐时仪,《汉语白话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再、归、元、但、同、闻、无、乃、翁、九州、即、颇、道、首、要、此、彼、颇等等,其实远不止于此,兹不赘述。这些使用至今的古词语就是上述晚唐五代至“五四”的近代汉语(古白话),与“五四”至今的现代汉语(现代白话)均有着胶黏一体的关系。以新中国以来汉语言使用的实践看,今天我们所定义的“现代白话文”的概念并不很准确,它其实包含了许多的古白话,大量的古白话词语因而就被认定是“文言”,由此也就派生出“文白混杂”说。
为明了这个问题,于此应澄清文言并非就等于“古代语言”的概念。“古代语言”里的“语言”是个大概念,其中的“语”是个小概念,即古代口语;其中的“言”亦是小概念,即古代书面语。狭义的文言专指古代一种书面语言,与之对应的是“古白话”,基本上是以后的口语和通俗文学。这两者可以类比西方“正式用语”(Formal Language)和“非正式用语”(Informal Language)的区别。这样我们就更为清楚一点:古代也有白话,现代也有文言。
当今我们常用的《汉语大辞典》收录古文字2835个、古文词语近1000组;另一为《现代汉语词典》,是新中国语文生活中用途最广泛的权威工具书,被公认为“最有学术价值和使用意义”的词典。据统计古词语在《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中有9816条,几占所收词条的五分之一①,足见它与方言词、新词语在国文生活中占有同样重要的地位。从语言实践上说,新中国以后我们文字交流的文言常用字有1400多个,由历年中、高考文言文考试出现的篇目进行验证,得到150个中学文言文字必考。其中仅初中教学列出的常用文言虚词为25个:(一)之、(二)其、(三)以、(四)于、(五)而、(六)则、(七)者、(八)也、(九)焉、(十)因、(十一)且、(十二)乃、(十三)矣、(十四)乎、(十五)所、(十六)哉、(十七)夫、(十八)遂、(十九)岂、(二十)然(二十一)故、(二十二)苟、(二十三)会、(二十四)或、(二十五)诸。
于此不妨假想,倘若在当今文字交流中去掉了数千个被称之为“文白混杂”中所谓“文”的古白话字词,则会如何?无疑将会使我们的语言使用陷入非常尴尬的境地,文将不文,志将不志。
因而,由大量的史志著述、应用公文、教科书籍、科普论著等的书面语言使用上足以查实,我们今天的现代汉语书面语中其实有着很多文言成分。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副院长孙德金对此曾作论述:现代汉语书面语是在近代白话的基础上,融合了文言、方言及其他语
① 中科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商务印书馆,2016年9月
言(主要是以英语为主的西方语言)的成分,经过百年多发展而成的。在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文言语法成分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是现代汉语书面语正式、典雅语体风格的主要决定因素。这些文言成分并非外加的,不是因为仿古、转文而使用的,而是现代汉语的书面表达(尤其是比较典雅、庄重的书面表达)所必需。
譬如现代书面语中,双音复合词中保留着大量的文言词类活用现象,“败家”“健身”“亡国”“干杯”“圆梦”都是使动用法;“夹攻”“奔袭”“吻别”“淋浴”“代购”都是文言的动词作状语用法;“蚕食”“庭审”“春运”“拳击”“心算”“病退”都是文言的名词作状语用法;“马匹”“车辆”“人口”“花朵”“纸张”都是文言的“名+量”用法①。
又如“于”“且”“以”“则”等为很常用的文言虚词,今天在一般情况下会用现代汉语的虚词代替,“于”换成“在/至”,“且”换成“而且”,“以”换成“用”,“则”换成“规则”。但是在某种语境下仍然要保留这些文言虚词的原意,如“高于一切”“苟且偷生”“以少胜多”“心烦则乱”。而且,即使在口语中有的还不可替代,如“十分之三”,“之”不能换成“的”;“以国家利益为重”,“以”不能换成“拿”。
语法格式是这样,词汇更是如此。很多文言词在现代汉语中虽不单用,但作为语素还很活跃,如“奥”可以构成“奥秘”“奥妙”“奥义”“深奥”等。有的词在历史上早已被替换,如“舟”已被“船”替换,但在现代汉语中,有时还必须使用旧词,如“扁舟”“诺亚方舟”“神舟七号”②。而在成语中保留文言词语则更多,如“亘古未有”“集思广益”“坚贞不屈”“名落孙山”“破釜沉舟”“名列前茅”等等。这些都是史志著述行文中常用文言词语,当代白话常无法替代。
2018年笔者主编的国家历史文化名村《鹏城村志》在复审时,就文中表述的“中国大陆1.8万公里海疆,因戍边筑堡海防而演就成村者,厥惟明洪武所建惠州市平海古城及同期所建深圳鹏城村”,以及志稿中的其他一些文言词语,如“为生存计”“盖因海防,乃筑城堡”“倭寇乃退”“析东莞县置新安县”等,被评审者评定为“文白混杂”。察古今国文,文言运用于方志久矣。作为新编地方志书从来不应陈陈相因、泥古不化,“你我一个样、彼此差不离”,既无自己的特色,亦无自己的语言风格,修纂出来的志书千头一面。读许多方志就如清水面条,无盐无油无佐料,食之乏味,仅可充饥。有鉴于此,为突出特色、分见你我,方志学界近些年来一直倡导创新,包括在语言的文采上亦应文笔各显。当今以现代白话文为主体的典籍譬如新方志,即便有一些文言的成分,我们从不应认为它的出现是突然,也不应认为是一件多么反常的事情,而应认定它是中华母语的传承和延续,
① 史维国,《现代汉语中的古代元素》一一文言与白话的有机融合,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6月
② 蒋绍愚,《也谈文言和白话》《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依然是国文。事实上许多文言成分积淀在今天的日常语言中,已经成为现代汉语的有机组成。
新中国两轮大规模修志近40年,“文白混杂”说令人困惑已久。窃以为新方志行文摒弃“文白混杂”的主要目的,怕是生恐一般民众难读难懂,这倒是有些杞人忧天。如果说文言文“在朝”,是文人士大夫之间的语言交流,那么“在野”的黎民能否且应该接受一些文言表达?以当今的文化现象来看,我们切莫低估了广大百姓的阅读和鉴赏能力。新中国开始尤其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教育事业的振兴推进,国民整体文化素质已大大提高,阅读带有一些文言的当代文章已不是什么困难,况乎地方志?即便在旧昔,一般老百姓观赏古装戏曲,尽管唱词与念白多古语,但却津津乐道、乐此不疲,并不曾有“听天书”的感觉。
当今国之元首习近平、李克强不仅十分关注地方志,还深黯中国传统文化,无论公开言说、小场即兴,常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出口成章,显示出深厚的国学功底。中华书局2002年版《平遥古城志》,原中国地方志协会学术委员、南开大学教授、地方志文献研究室主任来新夏(已故)为之作序,开篇言道:“全国地上文物山西约居十之七,而首登世界文化遗产宝册者,厥惟平遥。平遥之所以获此殊荣者,以其为古城也”。短短数语,文言意味十足,并不妨碍我们读懂其意。又如赵本山东北方言的小品,却能引来全国的一片笑声,说明人人皆懂。
不惟文言所蕴含的历史、文采、哲理、境界当为我辈深入研习,古人对于文字考究的认真执著亦堪为我们作文的楷模。唐代诗人卢延让《苦吟诗》说:“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裴说《洛中作》说:“莫怪苦吟迟,诗成鬓亦丝”。贾岛《题诗后》说:“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诗人为让自己的诗文生动传神、言简意赅,常会对诗文中某些词语和语句反复斟酌,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王安石“春风又绿江南岸”,欧阳修“环滁皆山也”,一“绿”字,一“环”字,一字点睛,精妙绝伦。
三、文言与白话的走向
汉语“文白”的转变是在文言和白话此消彼长过程中形成的。秦汉以后文献中的口语成分演变成了古白话,其由附庸于文言的地位到最终取得独立“割据”地位的发展过程,反映出随着时代的发展,最终也是汉语书面语有意识选择白话的必然结果。但文白之转,并不就等于文言完全退出汉语的历史舞台。
语言是人的语言,语言发展演变自然不能脱离人、不能脱离社会。当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不断发展、新事物不断出现时,语言必适应社会发展,适应交流的需要。为更好地表达思想,表述方式也必须有所改进。由于社会的变革、不同文化的碰撞交融,人们主体意识逐渐增强,因此也越来越渴望表达自我,这些都是文言到白话转变的成因。而转变不等于同化,徐时仪曾论述:“文白演变是同一语言内口语形式和书面语形式的语体转型,既是一种语言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既是表达功能的需要,也是雅俗相融的价值取向”①。普读大量新编地方志书不难发现,现代白话文的表述既有“阳春白雪”式的文言成分,也包含“下里巴人”式的当代口语白话成分,有本土,亦有外来,这当是不同文化交融使然。
“文白”转变既是语言自身发展的规律,也是社会发展变化带来的必然。“文白”转变涉及语言、人、客观世界三者间的复杂关系,同时也反映出不同阶层、不同文化的人们使用同一种语言的发展趋势,即精英文化与平民文化以及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彼此交融的价值取向。譬如新编地方志,既是为了服务于官方的决策,实现“资治”之目的,曰“在朝”;同时也是满足社会民众阅读需要,从而达到“教化”之功效,曰“在野”。
而时至今日,这种大量“文白”并存的事实下仍有不少人这样轻率的判识:文言为古代所用,白话为现代所用。这实乃认识上的误区,实非历史唯物主义史观。
白话与文言同源中华母语,同根同族,只不过表现形态有所不同。从同根同源、一脉承袭的角度,我们反对将文言与白话极端地分裂为两重天一一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人为的将国家的母语分判为此与彼,这是罔顾历史,是对历史的大不恭。笔者曾将这种文言退位白话兴起的现象表述为:“文言式微白话起,春兰秋菊不同时”,如果说现代汉语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那么文言就是其根其本,根之不存,枝将不附;如果说现代汉语已是大江硕湖,那么文言恰似其源其流,泉枯流涸,江湖难盈;如果说现代汉语已经历一个世纪的风雨,长成为健壮的小伙、婀娜的姑娘,那么文言正是其父其母,未有娘亲的乳汁哺育和老爹的谆谆教诲,焉有今朝?
即便“文言”的退位,在当代的书面交流中,部分文言渗入白话其里仍使得语言变得更为典雅、庄重,故当今白话文就有了文雅和平俗之分,且雅俗并存。现、当代著名的白话文作家如胡适、鲁迅、郭沫若、周作人、林语堂、郁达夫等,其文无不显透出深厚的文言功底。纵使到新文化运动之后已经是白话的天下,写小说都是用白话,不再用文言,但一些古文根底深厚的作家所写小说里也会有不少“文”的成分。以茅盾的小说和赵树理的小说比之可以明显看出,前者“文”的成分要高于后者。
钱玄同在《钱玄同文集》中提到:如果把“国语”仅仅限于普通会话,仅仅以一般民众的知识为标准,只会“国语更为贫弱”,而“理想的国语”要“活泼、自由、丰富”,为此就要把“古语、方言、外国语等”加以融合②。
惜乎,面对万卷古书、浩瀚遗产,当前真正能接受、研读中华母语并于中汲取营养的人并不为多,将来也未必见多。可是能够断言,白话绝不可能发展到脱离母语而独立、唯一存
① 徐时仪,《汉语白话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② 钱玄同,《钱玄同文集》(第五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在的地步。盖白话的发展也正是因了文言的匡扶、借鉴,以及不断从文言中汲取营养的过程,本质上并未变种,依然是母语的延续和发展。“五四”以后所谓的文言退位,无非是调换了角色,即由主角变成了配角而已,文言的精髓部分仍在白话中继续发挥着独有的作用。
认定了文言乃中华母语之精髓,欲了解和承传中国传统文化就不能不懂文言。尤其从事地方史志、文化、教育、社会、科研工作者都肩负着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任,当既加强文言研读且善加运用。掌握一些文言知识不仅仅满足使现代白话文厚润,倘如在作品中闹出一些有悖传统文化常识性的语错就更不该。央视2020年2月开始每日上午热播的电视剧《破局》,本为反映民国时期的事情,却出现由左至右的横匾“济民药房”。2019年6月,笔者在《贵州自然资源年鉴》启动培训会作授课期间,抽暇到当地一公园游览,发现该园内一块牌子上书:“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无幼,以及,人之幼”字样。央视有些主持人常将安徽两座历史文化名城亳州、六安念作“hao(毫)州”、“liu(六)安”。
当前短短几十年,网络时代的交流跨越了空间的限制,各种表达方式的空前发展令语言变得异常活跃,许多新词汇、新概念层出不穷给现实生活中的交流带来了很大乱象,一些从不上网的人或一个时期不上网的人就会对一些新的语言摸不着头脑。譬如:埋单、酷、帅呆、吐槽、碰瓷,蟑螂不叫蟑螂,叫一一小强;东西不叫东西,叫一一东东等等。如果这种趋时生造的语言被写进国文,不加注释的流传后世,将来后人还是否能够理解所要表达的含义?这样的违规则语言无疑将会给母语的传承带来极大的麻烦。据说在英国,现在的孩子已经读不懂莎士比亚的著作。而我们目前的情况更为糟糕,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不太能理解年轻人的话语。
2017年2月20日,作者毛莉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文说:“语言文字使用不规范。广告商随意玩弄文字游戏,粗俗怪诞之语充斥网络,网络语言在书面语中滥用,各种媒体中文本的庄重性、严谨性不足……”①。尤令人担忧的是,当今一味追求颠覆、摈弃规范的做法使汉语使用已呈违规泛滥状态,无怪乎有学者惊呼,当下汉语陷入了“草率化、朦胧化、粗鄙化、游戏化”四大危机。
“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至今已一个世纪。在这一个世纪中白话文有了长足的发展,产生了一些白话佳作,但白话文的发展是否可以就此止步?当然不可。在肯定白话文发展成果的同时,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其很大的不足。实事求是断论,当今社会浩瀚似海的国文里,平庸作品远多于佳作良作,新编地方志书亦无例外。“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先师孔子的圣言于今仍不失为至理,完全照当前口语写文,会使我们的书面语愈来愈贫弱苍白。一
① 毛莉,《维护汉语的通用语主体地位》,中国社会科学网一一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02月20日
言以蔽之,现代白话的书面语应该基于口语而又应高于口语,在“高于”这一点上,确实尚需全社会从事文字者的戮力奋勉。
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先生有一名言:“中文乃一切中国人心灵之所托,只要中文长在,必然汉魂不朽”①。中华母语是我们的生活之根,是我们的文化之根。汉语作为我们的母语是我们生命和精神的依托根本,没有汉语的这一价值,我们将失去一切。虽然在汉语的传承与发展中,而今古老的文言被置身于传统与现代的漩涡,在守望着时代的起落沉浮,但它所承载的不仅仅是一个民族的荣辱兴衰,更是一个文明古国永远不可忘却的历史。如果我们失却了作为一个大国的传统文化母语之精髓,我们真的就成了数典忘祖的“新文盲”。
① 余光中,《我的国文启蒙》,《语文世界《初中版》,2018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 徐时仪:《汉语白话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2] 蒋绍愚:《也谈文言和白话》《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3] 张中行:《文言津逮(张中行作品集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6月
[4] 吕叔湘:《近代汉语读本·序》,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
[5] 冯胜利:《汉语书面语的历史与现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6] 张中行:《文言与白话》,黑龙江出版社,1988
[7] 钱玄同:《钱玄同文集》(第五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8] 史维国:《现代汉语中的古代元素》一一文言与白话的有机融合,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6月
本文刊载《深圳史志》2020年第四期